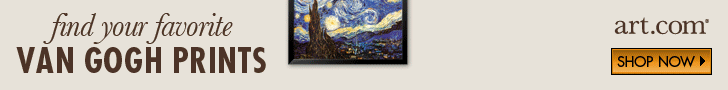
 |
"对于我来说,我的思绪常常相当地不安宁,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总是不够平静;那些让人痛苦的失落,灾祸和变故让我的画家生涯无从获得完满的,自然而然的发展。"
文森特.凡高 |
 |
以下的生平传记绝不是一个对凡高生平完整而全面的探究和介绍。它仅仅按年代记载了凡高生命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在“书籍”这一部分我罗列了各种版本的凡高传记,并标明了我特别推荐的版本。其中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是Jan Hulsker的《文森特和提奥.凡高:两兄弟传》──强烈推荐。
对于凡高生平纪年表,请参考凡高纪年表。
文森特·凡·高于1853年3月30日出生于荷兰的格鲁特·曾德特。 凡高的生日正是他那一出生便夭折的哥哥的周岁忌日,他的哥哥是凡高太太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名字也叫文森特. 许多人猜测文森特.凡高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与他是夭折哥哥的“替身小孩”,而他们又同一天生日、同一个名字有关。然而这一观点至今未被证实,而且也没有支持这一观点的历史事实。
 凡高的父亲是荷兰新教牧师提奥德罗斯·凡高(Theodorus van Gogh, 1822-85),母亲是安娜·克纳莉亚·卡本特斯(Anna Cornelia Carbentus, 1819-1907)。很遗憾,对于凡高十岁以前的生活目前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凡高在泽文伯根的寄宿学校学习了两年,然后进入蒂尔堡的威廉二世国王初中继续学习了两年。1868年,凡高在15岁的年纪里离开了学校并从此再没有回去。
凡高的父亲是荷兰新教牧师提奥德罗斯·凡高(Theodorus van Gogh, 1822-85),母亲是安娜·克纳莉亚·卡本特斯(Anna Cornelia Carbentus, 1819-1907)。很遗憾,对于凡高十岁以前的生活目前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凡高在泽文伯根的寄宿学校学习了两年,然后进入蒂尔堡的威廉二世国王初中继续学习了两年。1868年,凡高在15岁的年纪里离开了学校并从此再没有回去。
1869年文森特.凡高进入设在海牙的艺术品经销公司──古彼尔谢公司工作。凡高家族历来与美术世界保持着联系──凡高的叔叔科尔纳利斯(“科尔叔叔”)和文森特(“森特叔叔”), 都是艺术品经销商。他的弟弟提奥在成年以后也成为一位艺术品经销商,这些都对文森特后来成为一名艺术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森特在经销美术品的工作中还算成功。他在古彼尔谢公司工作了七年多,于1873年被调往伦敦分公司工作。在那,他很快便被英格兰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吸引。八月底,文森特搬到海克福特路87号居住,房东是尤苏拉·洛耶和她的女儿尤嘉妮。相传文森特曾经迷恋尤嘉妮,但许多早期的传记错将尤嘉妮的名字写成了她母亲的名字:尤苏拉。而这个让人们混淆了多年的名字问题最近又被加入了新内容,有人提出文森特从没爱上过尤嘉妮,而是爱上了一个叫卡罗琳·海尼比克的荷兰女子。真相如何至今未有结论。
文森特.凡高在伦敦继续居住了两年。其间他参观了许多画廊和博物馆,并成为乔治·艾略特,查尔斯·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忠实崇拜者。这些伟大的作家鼓舞了凡高,也影响了他今后的画家生涯。
年复一年,凡高和古彼尔谢公司的关系日益紧张了。1875年5月,他被派往巴黎分公司。随着岁月流逝,凡高每天和那些与他自己的艺术品味毫不相同的画作打交道,渐渐便不再感到高兴了。1876年3月底,文森特离开了古彼尔谢公司,他决定回到伦敦,那个他曾经生活了两年,其间大部分时间里非常快乐并收获颇丰的城市。
四月里文森特·凡高进入拉姆斯盖特的Rev. 威廉P.斯托克斯学校执教。给24个10岁到14岁之间的男孩子当班主任。在书信中文森特说他很喜欢当老师。此后他又到由Rev. T. 斯雷德.琼斯在艾尔斯沃斯开办的男校任教。业余时间里文森特继续参观画廊,又发现了许多他喜爱的美术作品。同时他还热衷于对《圣经》的研究--一遍又一遍地研读《福音书》。1876年的夏天是文森特·凡高的信仰发生转变的日子。虽然出生在神职人员家庭,但直到此时他才真正开始严肃地考虑献身宗教。
为了从教师转变为牧师,文森特要求Rev.琼斯允许他做更多的神职人员的工作。琼斯答应了他,于是文森特开始在特恩格林郊区内的祈祷会上执行宣讲。这些宣讲为文森特一直盼望的他的第一次礼拜日布道奠定了基础。虽然文森特对牧师职业充满热情,但是他的布道却很是枯燥乏味。和他的父亲一样,文森特对宣讲宗教有很高的热情,却缺乏生动精彩的表达能力。
文森特·凡高并不为在英国的失意而气馁,和家人共同度过圣诞节后,他留在了荷兰。1877年初,他在多德雷赫特书店打了一阵短工,然后于5月9日前往阿姆斯特丹准备大学神学专业的入学考试。在那里文森特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和数学。但由于基础太差,在补习了15个月后,他最终放弃了求学的打算。后来文森特形容这是他生命里“最糟糕的一段日子”。11月,在三个月的实习后,他仍没能通过福音传教学校的牧师资格考试。文森特没被这一系列的失败动摇,最终他谋到一个见习布道师的职位,工作地点在西欧最排外最贫穷的地方:比利时勃利那日煤矿。
 1879年1月,文森特在瓦斯麦斯矿工村开始了对煤矿工人和家属的布道工作。文森特感到自己在情感方面与矿工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同情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他们精神上的引导者,以减轻他们沉重的生活负担。当文森特开始把自己的衣服和食物分给贫穷的矿工家庭时,他的这种无私的热情高涨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不幸的是,教会的人士无视文森特善良高尚的初衷,而是坚决反对他对自己奉行的禁欲主义,在七月里将他从见习牧师的职位上驱逐。凡高拒绝离开当地,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叫库斯麦斯的村子,生活得贫寒而艰辛。以后的一年里文森特度日如年,虽然他不能再象真正的牧师那样帮助村民,但仍然选择了继续做村民中的一员。一天,文森特迫切地想去拜访朱尔斯·布雷顿, 一位他十分敬仰的法国画家。兜里揣着10个法郎,他徒步70公里到了布雷顿居住的法国的库里耶尔。当他终于来到布雷顿门前时,却因为极度的羞怯而没有勇气抬手敲门,只得无比沮丧地回到了库斯麦斯。
1879年1月,文森特在瓦斯麦斯矿工村开始了对煤矿工人和家属的布道工作。文森特感到自己在情感方面与矿工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同情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他们精神上的引导者,以减轻他们沉重的生活负担。当文森特开始把自己的衣服和食物分给贫穷的矿工家庭时,他的这种无私的热情高涨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不幸的是,教会的人士无视文森特善良高尚的初衷,而是坚决反对他对自己奉行的禁欲主义,在七月里将他从见习牧师的职位上驱逐。凡高拒绝离开当地,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叫库斯麦斯的村子,生活得贫寒而艰辛。以后的一年里文森特度日如年,虽然他不能再象真正的牧师那样帮助村民,但仍然选择了继续做村民中的一员。一天,文森特迫切地想去拜访朱尔斯·布雷顿, 一位他十分敬仰的法国画家。兜里揣着10个法郎,他徒步70公里到了布雷顿居住的法国的库里耶尔。当他终于来到布雷顿门前时,却因为极度的羞怯而没有勇气抬手敲门,只得无比沮丧地回到了库斯麦斯。
从那时起,文森特开始画煤矿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记载他们艰辛的生活。这是文森特·凡高生命的转折点,他从此认定了自己下一个,也是最终的事业目标:做一名画家。
画家的起步
1880年秋天,在勃利那日做了一年多的贫民以后,文森特前往布鲁塞尔学画。由于有了弟弟提奥在经济上的资助,文森特找回了学画的勇气。文森特和提奥从孩提时代起就亲密无间,这种亲情一直延续到他们成年以后,人们能从他们的通信中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兄弟情谊。我们今天能了解到的凡高对自己的作品及生活的评价,绝大多数来源于这700余封通信。
1881年对于文森特.凡高来说可谓不平静的一年。他申请进入布鲁塞尔埃科尔·比由克斯美术学校。传记作家赫尔斯卡和特拉巴特对凡高这段求学经历有不同的看法。特拉巴特认为凡高曾在该美术学校默默无闻地学习过一段时间,而赫尔斯卡则认为文森特的入学申请根本没有被接受。总之文森特仍坚持自学,他的参考书是让·弗朗索瓦·米勒的Travaux des champs,查尔斯·巴古尔的Cours de dessin等等。暑期开始,文森特再次回到当时已经搬到荷兰埃顿的父母身边。在父母家中,凡高遇见了他的表姐柯妮莉亚·阿德莉亚娜.沃斯-斯特利克(昵称“柯怡”)。柯怡(1846-1918)当时新寡,自己抚养她的小儿子。文森特爱上了这位表姐,而她却拒绝了他的求爱,凡高因此遭受沉重的打击。这件不幸的事导致了其后的那件凡高一生中最难忘的事件。被表姐回绝以后,文森特决定到她父母家里寻求支持。他的舅舅不允许文森特见自己的女儿,可文森特决心已定,他将自己的手搭在油灯的排气口上,让它被烧着,得不到见柯怡的允许,他就不不打算把手从火焰上拿开。可是柯怡的父亲只是轻松地将油灯吹灭,便使文森特的威胁行动迅速夭折。文森特倍感耻辱地离开了。
尽管在和柯怡的感情问题上受挫,又同父亲关系紧张,文森特却从他的表兄安东·玛维(1838-88)那里得到了鼓励。玛维是个成功的画家,他从自己的家乡海牙给文森特寄来自己最初的一批水彩画──于是文森特开始了对色彩的研究.文森特是玛维的忠实崇拜者,对玛维能给予他的任何指教都心怀感激。他们的相处一直很融洽,但自从文森特开始和一名妓女交往以后,便不再如此了。
 文森特·凡高1882年二月底在海牙遇见了克拉斯娜·玛利亚·霍尔尼克(1850-1904) 。在此时她正怀第二个孩子。这个女人, 被人称作”西恩”的, 不久便搬来与文森特同住。文森特和西恩同居了一年半, 他们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 部分原因是这两个人都脾气暴躁, 还有就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一直十分贫寒。文森特在给提奥的信表达了他对西恩感情的投入,尤其是对她的孩子们的投入, 虽然美术始终是他最关切的──这种关切在任何其他事情之上,包括温饱。西恩和她的孩子们为文森特的许多画做过模特, 在这段日子里,他的美术天分逐渐得到了发展。他早期的,以勃利那日煤矿工人为主题的略显粗糙的素描为日后更加精细且充满感情的作品奠定了基础。以素描《西恩,和小女孩坐在篮子上》为例,文森特精确地描绘了一个妇人静静地做着家务,心中深藏着一种绝望的情绪──这种情绪足以用来形容凡高和西恩共同生活的19个月。
文森特·凡高1882年二月底在海牙遇见了克拉斯娜·玛利亚·霍尔尼克(1850-1904) 。在此时她正怀第二个孩子。这个女人, 被人称作”西恩”的, 不久便搬来与文森特同住。文森特和西恩同居了一年半, 他们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 部分原因是这两个人都脾气暴躁, 还有就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一直十分贫寒。文森特在给提奥的信表达了他对西恩感情的投入,尤其是对她的孩子们的投入, 虽然美术始终是他最关切的──这种关切在任何其他事情之上,包括温饱。西恩和她的孩子们为文森特的许多画做过模特, 在这段日子里,他的美术天分逐渐得到了发展。他早期的,以勃利那日煤矿工人为主题的略显粗糙的素描为日后更加精细且充满感情的作品奠定了基础。以素描《西恩,和小女孩坐在篮子上》为例,文森特精确地描绘了一个妇人静静地做着家务,心中深藏着一种绝望的情绪──这种情绪足以用来形容凡高和西恩共同生活的19个月。
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他的艺术生涯里,1883年都是凡高的又一转折点。文森特从1882年起开始画油画,但直到1883年,他才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美术载体。随着他绘画技巧的提高,他与西恩的感情开始恶化,九月里他们终于分手了。从勃利那日的失败开始,文森特总是习惯于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从痛苦中摆脱。带着无比的遗憾,尤其是对西恩的孩子们的眷恋,文森特在九月中旬离开了海牙,去了德伦特,荷兰北部一个荒凉的地方。接下来的六个月,文森特过着流浪的生活,他走遍了整个德伦特地区,边流浪边用素描和油画描绘所到之处的风景和当地的居民。
1883年底,文森特再一次回到父母家中,那时他们已经搬到了纽南。接下来的一年文森特·凡高不断完善自己的技艺。这一时期他画了许多油画和素描作品:纺织工,纺线工以及其他的肖像画。当地的农民成为他最中意的绘画对象──部分是因为凡高觉得自己和这些贫苦的体力劳动者有着紧密的联系,部分是因为他对画家米勒的无比的崇拜,米勒自己就曾画过许多在田间劳动的农民,画中饱含伶悯之情。文森特的浪漫史在那年夏天又续演了一段戏剧性的但十分不快的故事。玛高特·博格曼(1841-1907)住在文森特父母家隔壁,她爱上了文森特,并在这场情感剧变之后试图服毒自杀。这件事使文森特倍受折磨。玛高特最终恢复了健康,但这次经历让文森特沮丧了很久,他在书信中曾多次提起这件事。
转折点1885:最初的力作
1885年最初的几个月,凡高继续画他的农民肖像系列。文森特把这看作“学习”,他在通过这些作品进一步完善绘画技巧,为他迄今为止最雄心壮志的作品做准备。文森特在3-4月间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学习,他父亲在3月26日的故去曾短暂地中断过他的学习。文森特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几年里关系始终很紧张。虽然文森特对父亲的去世并非不难过,但他从情感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因此不久他便开始继续作画了。
 多年的辛勤工作,持续不断的技巧改进和对新画法的学习──这一切努力就像石头,堆砌成文森特进步的台阶,让他画出了他第一幅伟大的作品:《吃土豆的人》。
多年的辛勤工作,持续不断的技巧改进和对新画法的学习──这一切努力就像石头,堆砌成文森特进步的台阶,让他画出了他第一幅伟大的作品:《吃土豆的人》。
1885年4月,文森特画《吃土豆的人》花了整整一个月。在画出最后的画布油画版本之前,他画了许多草图。《吃土豆的人》被认为使文森特.凡高第一幅代表作,他本人为这幅画的完成而倍受鼓舞。虽然这副画遭到了许多批评(文森特的朋友和同行安东·凡·拉帕得(1858-1892)很不喜欢这幅画,他的评价险些结束了两人的友谊),文森特又生气又有些沮丧, 但他仍然对这样的结果感到高兴,并从此开始了更加自信并且技巧更加娴熟的绘画事业的新阶段。
凡高在整个1885年里继续作画,但又一次地变得欲罢不能,又要寻找新的刺激。1886年初他被安特卫普艺术学院短期课程录取,但大约4周后便因为无法忍受授课人狭隘严格的授课方式而退学。一生中文森特经常批评刻板的正规学习,他认为正规教育是实践的廉价替代品。文森特花了五年时间辛苦地琢磨自己的绘画天分,随着《吃土豆的人》的诞生,他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先锋画家。但文森特仍继续力图完善自己,去了解新的思想,去探索新的技巧,努力要成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画家。在荷兰他已经尽他所能,学到了他能学到的一切。文森特离开荷兰去了巴黎寻找新的答案和印象派画家一道。
新的开端:巴黎
文森特·凡高曾在1886年初给他的弟弟提奥的信中反复强调,想要提奥相信巴黎才是他真正的归宿。提奥对兄长鲁莽的性格十分了解,坚决反对他的看法。和以往一样,文森特没有在乎,在三月初先斩后奏地来到了巴黎。提奥没有办法,只好收留了他。
凡高在巴黎的岁月将他变成了一个艺术家,这段日子是那么让人着迷。但遗憾的是在巴黎的两年却又是文森特生活的文字记载最少的两年--因为传记作家们过分依赖文森特和提奥两人的通信来确定事实,而兄弟俩的通信在文森特搬到提奥在巴黎蒙格玛丽区勒匹克街54号的公寓后,便中断了。
文森特在巴黎的日子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位画商,提奥跟美术界有许多联系,这样文森特便有机会结识了当时震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的许多画家。凡高在巴黎的两年是在参观早期印象派画展(这些画展展示了德加,莫奈,雷诺阿,皮萨罗,修拉和西斯里的作品)中度过的。毫无疑问凡高在画法上受到了印象派画家的影响,但他仍然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两年中凡高都借鉴了印象派画家的画法,但却从没让他们强大的影响力征服自己。
1886年文森特一直喜欢在巴黎郊外作画。他的调色板开始发生转变,那较阴暗的传统荷兰色彩不见了,逐渐趋向亮丽的印象派的颜色。正是在巴黎的这段时期,文森特开始对日本美术产生了兴趣,为他的画风又添加了一些浓重的色彩。日本当时刚刚在几个世纪的封闭之后打开了国门,由于以前长期的闭关锁国,西方世界一下子迷上了各种各样的日本事物。凡高开始收集日本版画(现在成为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的馆藏),他这一时期的画作(比如《唐圭伊老爹肖像》)便反映出印象派明亮的色彩和鲜明的日本画风的影响。虽然凡高只临摹过三幅日本画,但日本画风对他的微妙的影响却是伴其一生的。
1887年是文森特来到巴黎成为一名画家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不论在情感上还是体力上都进一步消耗了文森特。文森特粗暴的脾气破坏了他和提奥之间的关系。文森特坚持要和提奥住在一起,他搬到提奥的公寓,以为这样既可以节省开支,又可以让他更加专心地作画。可是,住在一起却让兄弟俩产生了许多摩擦。此外,巴黎也自有她的诱人之处,这两年里文森特的身体糟到了极点:缺乏营养,过渡吸烟和酗酒。
在文森特一生,冬天的坏天气总是让他暴戾而且情绪低落。再没有比在绝好的天气里走出门外和大自然互诉心声更让文森特高兴的事了。不论是作画还是只是散散步,文森特·凡高都渴望见到太阳。在1887-88年巴黎阴冷的冬天里凡高变得烦燥不安。这种情形反复出现。凡高在巴黎的两年在他画家的人生道路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他已经得到了他渴望的东西,于是,该是重新启程的日子了。文森特在大城市里从没有过真正的幸福,他决定离开巴黎,去追赶太阳,去追随他的命运──去南方。
南方的画室
由于种种原因1888年初文森特·凡高来到了阿尔。对巴黎的狂躁和漫长的冬天的厌倦,让凡高选择了普罗旺斯的温暖阳光。此外,凡高一直想在阿尔建立一个画家联谊会,以使他在巴黎的志同道合的画家们有一个避难所,同时他们可以在此共同作画,为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持,互相帮助。1888年2月20日,凡高登上了从巴黎开往阿尔的火车,一路上他憧憬着自己光明的未来,欣赏着沿途旖旎的风光,越接近南方,他越觉得这风光更有日本风格。
毫无疑问凡高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对阿尔很是失望。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太阳,却发现被大雪覆盖的阿尔不同寻常地寒冷。这让抛开了一切来南方寻找温暖和勇气的文森特感到有些泄气。还好寒冷刺骨的严冬十分短暂,文森特开始创作他画家生涯里最受欢迎的作品。
气温刚刚回升,文森特立即开始了户外的劳动创作。请注意两幅倍受称赞的作品:素描《风景:小径和剪过枝的树木》和油画《有柳树的田间小径》 。素描作于三月,树木和田野都显出冬天过后的荒凉。而油画则作于一个月以后,画出了早春树上的新芽。这段时间凡高画过许多开花的果树。文森特对自己的创造力很是满意,就像那些果树一样,他感觉获得了新生。
 接下来的几个月十分快乐。文森特先是住在拉玛尔亭区10号的阿尔加萨咖啡馆的一间屋子里,5月初,他租下了那间著名的“黄房子”(拉玛尔亭区2号)作为画室和储藏间。文森特直到九月才肯搬进黄房子住,为了将它筹备成他的“南方画室”的基地。
接下来的几个月十分快乐。文森特先是住在拉玛尔亭区10号的阿尔加萨咖啡馆的一间屋子里,5月初,他租下了那间著名的“黄房子”(拉玛尔亭区2号)作为画室和储藏间。文森特直到九月才肯搬进黄房子住,为了将它筹备成他的“南方画室”的基地。
整个春夏,文森特勤奋地工作着,同时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提奥。如今凡高总是被看作一个性情暴躁而孤僻的人。但在那段时期他确实喜欢上了与人打交道,并且一直在努力结交朋友──既为了交朋友,也为了得到更多的模特。很多时候文森特深深地感到孤独,可他还是和保罗-尤嘉因·米列特和另一位轻步兵战士成了朋友,并为他们画了肖像。文森特从没放弃建立画家沙龙的想法,于是开始游说保罗·高更来南方和他一起工作。这主意看起来不太可行,因为高更的到来将进一步加重已经不堪重负的提奥的经济负担。
7月,凡高的叔叔文森特去世,留给提奥一笔遗产。这笔收入使提奥得以应付高更的到来。提奥开始不再只是一个兄弟,而又扮演起商人的角色来。提奥感到和高更在一起将会使文森特心情好起来,情绪会稳定下来,同时他也希望高更为补偿他的资助而交给他的那些画作能够卖出些价钱。和文森特不同,保罗·高更此时已经从他的作品中初尝到小小的胜利果实。
尽管提奥的经济状况稍有改善,可文森特还是老样子,用在日常生活上的钱远远少于他购买画具用的钱。由于过度的营养不良和超负荷的工作,凡高的健康状况在十月初开始恶化,然而高更决定来南方和他一起工作的消息使他倍受鼓舞。文森特勤奋地布置黄房子,努力想使高更感到他很受欢迎。10月23日早晨高更乘坐的火车到达了阿尔。
接下来的两个月对文森特·凡高和保罗·高更来说都是关键的同时又是灾难性的。起初两个人相处愉快,一起在阿尔周边的地方画画,讨论美术和他们不同的技法。然而,几个星期以后,坏天气来临了,两人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留在家里。和以往一样,文森特急躁的脾气(高更经常也是一样)随着天气变化着。由于只能在家里作画,文森特创作了一系列的肖像画,这些画鼓舞了他,他的消极情绪开始稳定下来。“我给整整一家人画了肖像”他写信告诉提奥(书信第560封) (560)。)罗林一家的肖像作品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的一部分。
可是凡高和高更的关系却在12月里逐渐恶化。他们之间激烈的争论越来越频繁──文森特形容他们之间“过电”。两人的关系随着文森特精神状况的恶化而每况愈下。12月23日,文森特·凡高,在极度癫狂的状态下,割下了自己的左耳的下半缘。他用刮胡刀割下耳垂,用布包了起来,将它拿到一家妓院,给一位妓女看。然后他踉踉跄跄地回到黄房子,晕倒在地上。警察发现了他并把他送往阿尔的赫特尔-迭戈医院。高更给提奥发了封电报,之后立即离开了阿尔回到巴黎,没有去医院看望凡高。凡高和高更此后仍经常联系,却再也没有相见。
住院期间,文森特一直受到费利克斯·瑞医生(1867-1932)的照顾。割坏耳朵以后的一个星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精神上对凡.高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他因为失血过多而痛苦万分,后来还由于严重的发病而不能行动。提奥匆忙地从巴黎赶来,他以为文森特就要死了。可是从12月底到1月初,文森特几乎痊愈了。
1889年最初的几个星期对文森特·凡高来说是艰难的。康复以后,文森特回到他的黄房子,但还需要经常去瑞医生那里做检查,同时更换缠在头上的纱布。文森特为精神崩溃以后的进步感到鼓舞,但经济问题却仍在继续困扰他。当他的密友,约瑟夫·罗林(1841-1903)为了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而决定举家迁往马赛的时候,他开始感到特别的沮丧。在阿尔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林都是文森特亲密而忠实的朋友。
从创作角度看,在1月和2月初里文森特的画作颇多,他创作了像《摇篮曲》和《向日葵》这样的著名作品。可是,2月7日那天又发病了,文森特认为自己是被人投毒了。他又一次被送往赫特尔-迭戈医院接受观察。凡高在医院住了10天,又暂时地回到了黄房子:“但愿这是好事。”(书信第577封)
在此之前,阿尔的一些居民已经开始对文森特的举止心存芥蒂,他们提交了请愿书表达他们的焦虑。请愿书被上交给阿尔市长,后被转交给警署负责人,他命令赫特尔-迭戈医院重新接收凡高。文森特在这所医院里继续住了六周,其间他被允许在有人监管的情况下出门──为了画画以及收拾自己的行李。对凡高来说这段日子作品很多但情绪却始终糟糕。和一年前一样,凡高重新开始画阿尔周围开花的果树。尽管文森特当时画出了他最出色的作品,他仍然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很不稳定。在和提奥商量过以后,他同意自愿地被送进位于普罗旺斯省圣雷米市的圣-保罗-德-矛索勒精神病院。5月8日,凡高离开了阿尔。
禁闭生活
到达精神病院后,文森特被泰奥菲勒·泽查利·奥古斯特·培伦医生(1827-95)照顾。经过检查和对继往病史的了解,培伦医生确认他的病人患有一种癫痫病──一个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最为贴切的诊断之一。这家疯人院一点也不是那种“蛇窝”,但凡高被这里其他病人的狂叫和糟糕的伙食所困扰。他失望地发现这里的病人整天无所事事──受不到任何形式的外界刺激。凡高接受的治疗之一是“水疗”,不停地将他浸在一个大浴盆中。虽然这种“治疗”称不上残忍,可它对缓解文森特的病情没有起到一点帮助。
几个星期过去了,文森特良好的精神状态一直很稳定,他被允许重拾画笔。医院的人们为凡高的进步(或者,至少是他没有再发病)而感到鼓舞,6月中旬,凡.高画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星夜》。
然而,凡高相对稳定的情绪并没保持多久,7月份中又一次发病使他不能行动。发病时文森特试图吞下自己的画作,为此他被关了禁闭并且不允许他接近画具。尽管他很快从这场事故中恢复过来,却始终打不起精神来,因为他无法再接触那带给他快乐并分散他的痛苦的东西:画画。又一周过去了,培伦医生让了步,允许凡高重新画画。他的工作的恢复伴随着病情的恶化。文森特给提奥写信,详细描述自己不稳定的健康状况;同一时期提奥也处在相同的境地里。提奥的体质一直很弱,整个1889年初他都在生病。
凡高两个月没有离开他的房间,在他给妹妹的信里写到:“当我在田野里时,觉得自己被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淹没,以至于我没有勇气再走出门去”(书信第W14封)。接下来的几周,文森特逐渐克服了对自己的焦虑情绪,再一次开始画画。这一回文森特开始打算永远地离开这家圣雷米的疯人院。他对提奥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提奥开始咨询了解治疗文森特的其它方法──这一次要在离巴黎近多了。
1889年余下的日子里凡高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一直稳定。提奥的病也大部分痊愈了,此时正在考虑和他的新娘结婚。提奥同时正在帮助奥科夫·矛斯组织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二十人"画展,其间将会展出文森特的6幅油画。文森特对这次尝试满怀热情,并且这一段创作力一直旺盛。在文森特和提奥之间频繁地通信,对作品参展的有关细节作了很多安排。
1889年12月23日,割耳朵事件后整整一年这天,文森特再次发病:他说这是一次“失常”(书信第620封)。这次发病十分严重,持续了将近一周。过后文森特很快地康复并开始继续画画──这一次他主要是临摹其他画家的作品,因为他又一次被囚禁,这既是因为他的精神状况不好,也因为天气。令人难过的是,凡高的病在189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一次又一次地发作。他的病的频繁地发作,使他一次比一次更加难以行动。让人觉得反讽的是,在凡高精神状况或许是最糟糕的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最终开始赢得人们好评了。然而这样的消息只是让文森特更加沮丧,同时他再一次有了离开疯人院回到北方的打算。
经过一番了解,提奥觉得对文森特最好的安排莫过于带他回巴黎,让精神病医生保罗·加歇(1828-1909)照顾他,加歇医生是同种疗法(顺势疗法)理疗师,住在离巴黎不远的瓦兹湖畔的奥维尔。文森特同意了提奥的建议,打点好了自己在圣雷米的行装。1890年5月16日,文森特·凡高离开了疯人院,坐夜车前往巴黎。
"这悲伤,将会永恒 . . . . "
文森特的巴黎之行平淡如水,提奥去车站接他。文森特和提奥,提奥的妻子乔汉娜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文森特·威勒姆(以文森特的名字命名)度过了愉快的三天。他从没有这样享受过这喧嚣而紧张的城市生活,不过文森特在巴黎还是感到有些压力,他选择离开,去一个更加安静的所在,瓦兹湖畔的奥维尔。
文森特到达奥维尔,马上见了加歇医生。虽然最初文森特对加歇的印象不错,他还是十分怀疑加歇的能力,甚至说加歇看起来“比我病得还重,我觉得,或者跟我不相上下。”(书信第648封 )。尽管文森特有担忧,他还是在亚瑟·古斯塔夫·雷瓦克斯开的小酒馆找了间小屋住下了。随即他便开始画奥维尔郊外的景色。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凡高对加歇的印象开始有了些转变,同时完全专注于他的绘画中。文森特很喜欢奥维尔,这里给了他在圣.雷米从未有过的自由,也给了他丰富的作画题材。文森特在奥维尔的最初几周过得愉快而平静。6月8号提奥和乔带着他们的小宝宝来到奥维尔看望文森特和加歇,这一天文森特和这一家三口度过得很愉快。种种迹象表明,文森特已经康复了──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整个六月,文森特精神状态都很好,而且作画效率极高,他画出了很多著名的作品(比如《加歇医生像》和 《奥维尔的教堂》)但在奥维尔的最初一个月的平静被侄子重病的消息打断了。提奥几个月来一直处在困境中:自己的事业和将来的不确定,持续的健康问题以及儿子的病。小宝宝康复以后,7月6日,文森特决定去看望提奥一家,于是搭上了早班火车。对于这次拜访的记载很少,只是很多年以后乔汉娜写到那天比较拘谨而且相当紧张。文森特终于感到受不了,很快返回了他平静的避难所奥维尔。
在后来的三个星期里文森特重新开始画画,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他挺高兴的。在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文森特写到:“现在我感觉比去年平静多了,我不得安宁的头脑也真开始平静了。”(书信第650封)。文森特被奥维尔的田野和周围的平原深深地吸引了,七月里他画了许多绚烂的风景画。对于文森特来说,生活看起来象要进入一种丰产的,而且──即使不是愉快的──最起码也是个稳定的模式。
虽然各种说法的时间次序有许多出入,但1890年7月27日发生的基本事实仍然是清楚的。那个礼拜天的黄昏,文森特带着他的画架和画具出了门,到田间去了。在田野里他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对着自己的胸口扣动了扳机。后来他挣扎着地回到了雷瓦克斯的小酒馆,瘫倒在床上,随即被雷瓦克斯发现。当地的大夫马泽利被请了来,加歇医生也来了。他们决定不从文森特的胸腔取出子弹。加歇给提奥发了封快件。不巧的是加歇医生并不知道提奥的住址,只得将信寄往提奥工作的画廊请他们转交。幸好这样做并没耽误太久,提奥在第二天的下午赶到了奥维尔。
文森特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始终和提奥在一起。提奥寸步不离他的兄长,抱着他,用荷兰语跟他讲话。文森特好像已经认命了,提奥后来写到:“他真的想死,当我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讲我们会帮他恢复起来,让他不再感到这样的绝望时,他说:'La tristesse durera toujours'(这痛苦将是永存的)。我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提奥,他兄长的始终如一的挚友和支持者,抱着文森特,直到听他讲了最后一句话:“但愿我就像这样地死去。”
文森特.凡.高死于1890年7月29日凌晨1点30分。因为文森特属于自杀, 奥维尔的天主教堂拒绝让他埋葬在天主教的墓地。但邻近的麦里镇收留了他,他在7月30日被安葬在麦里镇的墓地。文森特一直的好朋友,画家埃米里·伯纳德,在给古斯塔夫·奥维尔伯特的信中这样详细地记载了文森特的葬礼:
|
棺材已经合上了。我终于没能见到那个四年前充满期望地和我告别的人,我来得太晚了
在曾经放置他的遗体的屋子里挂满了他最后的画作,它们像绕在他周围的光环,这些画作所辐射出的天才的灵光,使我们这些在场的艺术们对他的死感到更悲伤。灵柩上只简单地盖了一层白布,周围摆满了大量的鲜花,他热爱的向日葵,黄色的大丽花,到处都是黄色的花。你会记得,那是他最喜欢的颜色,是阳光的颜色,他一直梦想着让阳光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存在于画家笔下。 在灵柩旁的地上放着他的画架,折叠凳和画笔。 来了很多人,大部分是画画的,我认识的有吕西安·皮萨洛和劳森特。其他人我都不认识,还有许多对他知之甚少的当地老百姓,也许和他打过一两次交道,他们喜欢他那样的善良和富有同情心···
我们就这样站在那儿,在这个盛着我们的朋友的灵柩周围,我们没有一点声音。我望着他临摹的作品:仿德拉克洛瓦的那幅非常美丽而忧伤的《虔诚》,和《高墙下绕圈的囚徒》,这幅画是在多雷一幅描绘可怖残暴的画启发下而作的,也是他自己的结局的预言。他的人生不正像这样,高高的监狱,高高的围墙──那样地高,而人们在绕着圈无休无止地走着,他们不正像那些可伶的画家们,象遭到诅咒的灵魂般在命运的鞭笞下艰难地前行? 三点钟,他的遗体被抬走了,朋友们将灵柩抬上灵车,队伍中有许多人流了泪。提奥·凡高,这个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哥哥,始终支持他为自己的美术事业而奋斗的弟弟,一直在令人心碎地啜泣··· 外面烈日当头。我们爬上了奥维尔郊外的小山,一路上谈论著他,谈他给艺术豪无畏缩的推动,谈他一直在酝酿的伟大的作品,也谈论他善待过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来到墓园,小小的一块新墓园里零星地竖着几块新碑。墓园在一个小山顶上,可以俯瞰广阔的蓝天下正待收获的麦田,有着他仍然会热爱着的一切··· 然后,他就被安放在墓穴里了··· 每个人看到这个场面都会落泪,这一天属于他的事情太多了,使人们无法不去想像他还在,还在为这些而感到愉快··· 加歇医生(一个热爱美术的,现在拥有最为出色的印象派作品的人)想为文森特致几句悼词,可他也是泣不成声,最后只是断断续续,充满混乱地说了些再见的话···(也许这才是对他最美丽的告别)。 加歇医生简短地介绍了文森特的奋斗和成就,说他的理想是多么高尚,而自己对他的敬意又是如何巨大(虽然他们相处时间很短)。加歇医生说到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只有两个目标,仁爱和美术。他认为无上崇高的是艺术,令他永垂不朽的也是艺术。 之后我们返回奥维尔。提奥多[原文如此].凡高痛不欲生;每个在场的人都被深深打动了,有些人出了门走到无尽的田野里,其他人回到了车站。 拉威尔和我回到雷瓦克斯家,我们还在谈论起他 . . . .1 |
六个月后,提奥·凡高也去世了,他先被葬于乌德勒支。1914年,提奥的妻子乔汉娜,她自己是文森特作品的如此全力而且懈的支持者,将提奥的遗体迁往奥维尔,将他葬在文森特的旁边。乔请人在这兄弟俩的墓碑间插上了一支从加歇医生花园中折下的常青藤。这些常青藤如今已像绿色的地毯一样,覆盖了文森特和提奥的墓地。
1. 卡赫尔. 文森特 4:《一位伟大的画家去世了》:文森特·凡·高悼念信 作者:Sjraar van Heugten and Fieke Pabst (eds.), (Waanders, 1992), pages 32-35.
参考书目
(翻译:XY)